原创 干货—老中医基层55年经验:断血流一味,治崩漏奇效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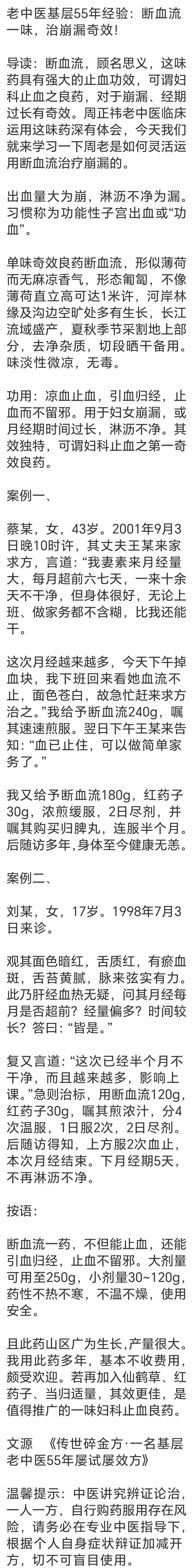
那是个下着细雨的午后,我和祖父站在老屋拆迁的废墟前。
“你看这些砖。”祖父弯腰捡起一块青砖,雨水顺着砖的棱角流下,“方的。”
我跟着捡起半块残砖,确实是方方正正的。不远处,几个滚落的石碾子散在泥泞里——它们是圆的,曾经是碾米的好工具,如今斜躺着,沾满污泥。
“圆的东西啊,堆不起来。”祖父用砖在掌心比划,“你看咱们这老屋,住了五代人,哪块砖不是方的?”
我想起老屋还在时的模样。祖父是木匠,一辈子没离开过这镇子。他做的家具方正,榫卯严丝合缝;他说话也方正,一是一二是二。镇上来过不少“能人”,王叔就是其中之一。
王叔是镇上有名的“圆滑人”。他会来事,见谁都笑脸相迎,递烟的动作永远比人快半步。那年木材涨价,所有人都愁眉苦脸,只有王叔四处活动,不知从哪搞来批“便宜货”。他劝祖父:“老哥,这世道得变通。”祖父拿起木头在鼻前闻了闻,又敲了敲,摇头:“这料被水泡过,不能用。”
王叔的笑僵在脸上:“就您较真。”
后来,用那批货的人家,不到三年家具就开裂变形。而祖父做的桌椅,三十年过去,依然结实。
雨渐渐密了。祖父领我走到老屋地基处,那里还保留着最底层的石基。
“你太爷爷留下的。”祖父蹲下,抚摸那些石头,“他说,做人就像砌墙,基础要方,才能往上垒。”
我想起父亲。他在城里做建筑工程师,有次甲方要求“灵活处理”材料标准,暗示可以“表示表示”。父亲连夜写了份报告,附上各种数据,第二天在会上说:“楼要是歪了,会出人命。”他丢了那个项目,却保住了心里那块方砖。
“你爸啊,像我。”祖父笑了,皱纹在雨水里深刻,“不懂转弯。”
可是去年那栋楼出了事,用的正是当年那个甲方坚持的“灵活方案”。调查组来找父亲时,他说:“我早说过。”
废墟那头开来推土机。工头过来打招呼,递给祖父一支烟:“老爷子,最后看一眼?”
祖父摆摆手,从怀里掏出个布包,层层打开,是把老旧的木工角尺。
“这是我师父传的。”他把角尺放在一块完整的青砖上,“你看,九十度,一分不差。”
角尺的铜边在雨里泛着暗光。我想起小时候,祖父教我认这角尺:“做人做到九十分不够,得九十分,就是直角,不能多一度,也不能少一度。”
“可现在人都喜欢圆的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祖父收起角尺,望向远处正在兴建的新楼:“楼越盖越高,哪栋不是方的?圆顶好看,可你要在圆顶上再加一层,试试?”
推土机开始作业。在轰鸣声中,那些圆石碾被轻易推开,而方砖垒成的墙基,需要反复撞击才能倒塌。
离开时,祖父最后回头看了一眼。废墟在雨中渐渐模糊,只有那些散落的方砖,依然保持着棱角。
“你记住,”祖父的声音混在雨声里,“圆的东西滚得远,可停下来的地方,自己说了不算。方的东西走得慢,但停在哪儿,就在哪儿扎根。”
那天晚上,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块砖。起初是圆的,在坡上滚得飞快,草木、溪流、风景都在后退。可当我想停下时,却停不下来,直到跌进深谷。后来我变成方的,每一段路都得一步步挪,有时被别的砖挡住,有时陷进泥里。可当我终于被垒进一面墙,和无数方砖在一起时,风雨来了,我们一动不动。
醒来时天刚亮。我走到书桌前,打开父亲去年送我的盒子。里面是祖父的角尺,还有张字条:“咱们家的人,不做滚石,只做基石。”
窗外,城市正在醒来。远方的工地上,塔吊正将方形的预制件吊起。那些构件在空中摇晃,但一旦落入位置,就会成为某个结构的一部分,支撑起重量,界定出空间。
我拿起角尺,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。九十度,一分不差。这个角度不圆滑,不讨巧,但它能垒起高楼,能丈量良心,能在风雨飘摇时告诉你:此刻站立的地方,就是你的位置。
雨停了,阳光照在角尺上,那道光也是直的——从过去照到现在,从现在照向未来,不转弯,不折扣,就像那些方方正正的人,走一条直直的路。
